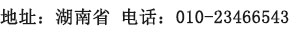记者陈宁通讯员史俊宋黎胜崔勇在手术中。浙江新闻客户端通讯员史俊摄这是人体内最精密的“仪器”——一天10万次的跳动,每跳动一次,都伴随着瓣膜的开合,片刻之间,血液流过1.5毫米的管道,向全身进发。成年人的心脏只有拳头般大小,它却“掌管”着关于生命的一切。有人形容心胸外科是最具挑战、最高难度的医学领域,一台较复杂的心胸外科手术往往持续5-10个小时,在这期间,手术刀下的“战场”只在毫厘之间。近日,记医院心胸外科副主任、副主任医师崔勇,在跟踪采访的24小时内,他是无影灯下有着精巧双手的主刀医师,是绿色通道旁匆匆而过的身影,也是休息片刻说起女儿莞尔一笑的父亲。这是一名心胸外科医生平凡的一天——“成为心胸外科医生是最骄傲的事”早晨7点,崔医院1号楼24楼心胸外科病区。医院的交接班时间还有40分钟。披上白大褂、带好口罩、拿起病案本,从事过这一系列必要而调单的动作之后,崔勇走向重病室,此时不到7点10分,窗外,这座城市才刚刚苏醒。重病室门口,一位头发花白的病人正在复健,见到崔勇后,她挪着脚步缓缓向前:“崔医生,原来的病房有点吵,我睡眠不好,方不方便换一间?”崔勇拿起手机向科室报备调整病房,很快,病人的烦恼解决了。“对医生而言,一身白大褂就是责任,他们有困难我想我都会尽力。”崔勇这样和记者说道。病房里很安静,氧气输送声、呼吸机的滴答声交错着,一起一落间,像是心脏跳动的的旋律。崔勇走向窗边的床位,身高超过一米八的他俯下身子,向病人询问着今天的身体状况。“咳嗽厉害吗?”“有力气就尽量下床走走。”在心胸外科,病人们多经历过开胸手术,身上都有5-10厘米正在愈合的刀疤,由于恢复周期长,不少人在手术后的一个月依然神经疼痛,只能小声说话。崔勇每次查房尽可能靠近病人,为了听得更清楚,也为了让病床上需要帮助的他们更加信任自己。跟着查房的,还有几名年轻医生,在距离生命和死亡都最近的心胸外科,一名医生的成长往往需要漫长周期。在国内,心胸外科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起步阶段后,正式迎来了90年代的黄金时期,并被誉为“皇冠上的明珠”。彼时,崔勇踏进校门成为了一名医学生。“心胸外科挑战医学巅峰,我一直非常向往。”年,正式成为一名心胸外科医生的崔勇做了自己主刀的第一台外科手术。在后来的14年里,全球医学在飞速发展,传统的心胸外科理念、技术也在不断更迭。一年年间,崔勇头上的无影灯变得越来越先进,手下的手术刀也在一代代更换,但他笑称自己依然是那个“一站到手术台前就能忘记吃饭、忘记睡觉、忘记上洗手间”的人,没有变的,是他那份“成为心胸外科医生是最骄傲的事”的初心。时间走到8点,崔勇暂时告别病房的工作,起身走向手术室,那是他最熟悉的“战场”,今天等待着他的,是一台心脏瓣膜置换与心脏搭桥的高难度手术。崔勇在准备手术。浙江新闻客户端通讯员史俊摄“没有什么比救死扶伤更有成就感”8点半前,崔勇准时到达手术室。心脏瓣膜置换和心脏搭桥,分别是心胸外科最高难度级别(四类)手术,今天的病人,要一次性连续完成这两台手术,崔勇告诉记者:“很难。”难在哪里?心脏瓣膜,是心脏的“阀门”,控制者血液的出入循环,一旦这扇门出现问题,将给人体带来致命影响。心脏换瓣术,一度被称为“涉险手术”,对心胸外科医生的技术有着极高要求。心脏搭桥手术是一项“精细活”,当人体冠状动脉发生狭窄、阻塞导致心脏供血不足时,需要在冠状动脉狭窄的近端和远端之间建立一座“桥梁”,使血液顺利绕过狭窄部位。这座生命之桥,要求心胸外科医生用比头发丝还细的线,链接两条不足1.5毫米的血管。而最难的,是手术关键过程需要停止患者心跳,期间患者的生命靠体外循环机维系。一般而言,停跳时间越长,给病人带来后遗症的几率就越大,因此,心胸外科手术的每一分钟都在赛跑。当记者问到崔勇是否紧张时,他说:“没有什么比救死扶伤更有成就感。”8点半,崔勇换上手术服,戴上手术帽,一墙之隔的手术室内,麻醉、护士、循环医师三个团队各司其职。9点整,手术正式开始。记者走进这间分秒必争的手术室,十多名医护人员紧张有序的配合着。9点到11点的近两个小时内,崔勇其他医护人员都在把心脏血管与一台庞大的体外循环机相连。在心脏停跳时间内,这台机器将“取代”心脏,保证血液有效循环。浙江新闻客户端通讯员史俊摄11点刚过,生命体征检测仪上,一条波浪线缓缓变平,心跳停止,整个手术室进入“倒计时”,一场争分夺秒的“战役”拉开序幕。崔勇小心处理心脏周围的粘连处,寻找着病灶,头戴探照灯的他看起来格外专注,那双心胸外科医生“鹰一般”的双眼,不放过任何一处异常。11点20分,手术室的电话响起,护士转告崔勇,并当一位病人出现胸闷,他快速做出初步判断,继续着手术。11点25分,经过仔细评估后,崔勇初步断定病人需要使用19号人工瓣膜,此时,手术正式进入关键阶段。身后的体外循环医师目不转睛监测着仪器,提醒着崔勇停跳时间。在并没有闹钟滴答声的手术室内,生命的声音清晰异常。每年,崔勇要完成余台心胸外科手术,平均每周6-8台,聚光灯下的他心无旁骛,架起一座座生命之桥。“我也许是个好医生,但我不是好父亲”整整5个半小时后,记者在护士办公室内再次见到了崔勇。“手术很成功!”顾不上吃护士递过来的盒饭,他先向记者传递了这个好消息。3点吃上午饭,已经是心胸外科的常态。一个半小时后,另一台手术等着崔勇,多年的手术经验,崔勇有一个少吃米饭的习惯,他告诉记者这是为了减少体内淀粉分解,降低犯困几率。心胸外科,一度是影视作品涉猎的热门领域。日剧《白色巨塔》,港剧《妙手仁心》,美剧《上帝之吻》都以心胸外科的医生为主角。但是崔勇打趣道:“我们的日常,并没有电视剧里描述的那样光鲜。”手术台之外,心胸外科要承担大量的急救任务。有数据显示,涉及到急救的主动脉夹层多数病例,在起病后数小时至数天内死亡,在开始24小时内每小时死亡率增加1%~2%。这就意味着,心胸外科医生要在极短时间内做出判断,抢救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的病人。短暂的休息时间内,崔勇与记者提到自己11岁的女儿,从她出生起,父女俩见面的时间就非常少。“也许我是个还不错的医生,但我不是一个好爸爸。”但每每看到需要帮助的病人,崔勇还是一次次选择牺牲与家人团聚的时光:“病人把性命托付给我,我要对得起这份信任。”崔勇24年的医学生涯,也是心胸外科不断面临挑战和创新的24年。随着腔镜技术的发展,微创手术取代了越来越多传统手术。但是,由于心胸外科的特殊性,这里的大部分手术还是要留下创口。如何让病人们恢复的更快,也是摆在心胸外科医生面前的一道难题。“我们依然要不断攀登,前方还有一座座的高峰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