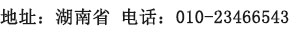在家隔离以来就没有写过东西,人在四堵墙里关着,脑子也被关上了,每天的日程大概就是工作-陪猫玩-工作-吃饭-工作-陪猫玩后睡觉。说起来,家猫这种生物,真是耐得住无聊啊,每天吃喝拉撒溜圈就在那一间屋子里。但转念一想,体积同比缩放一下,可能房间之于猫咪,类似于操场之于人类?可操场能有多大呢。更加庞大的生物,比如大象,看人类可能也会这样想:就那么小一个房间,子弹头一样小的地铁,马桶一样窄的工位...“人类真是耐得住无聊啊”。
可是要说“无聊与否”,光拿动物体积和活动空间来做比较是不够的。还有个很重要的因素是“活动能力”。比如说吧,跑步很烂的人看到米的跑道腿就发软,但是谷爱凌等运动健将看到北京地图,整个斗志满满。也就是说,活动能力决定了动物对空间大小的主观感受,但另一方面,空间大小反过来影响动物的活动能力。最好的例子就是野猪和家猪。本是同根生,野猪撒欢儿跑山头,家猪转身儿墙碰头。
猪圈里的猪,多么可怜又可悲啊,可在我最爱的两位作家:莫言和王小波的作品中,竟然被描写得那么神通广大,“特立独行”,甚至有些不可一世。
在莫言的《生死疲劳》里,那猪十六作为一只本应该专项繁衍后代的种猪,居然有审美(赏月)、懂改造(松软的杏叶儿做床)、运动能力强(会上树、会打架),仗义(和敌猪相救于江湖),更是一只有追求有价值观的猪(舍身相救溺水儿童),尽管最后壮烈牺牲,未能颐养天年,但绝对是活出了风格,活出了水平。
《一只特立独行的猪》里,王小波的那位“猪兄”本是只肉猪,却“又黑又瘦,两眼炯炯有光”,一米高的猪栏一跳就过。奈何肉猪就是肉猪,吃了国家的粮,就得给国家出肉,这是它的使命。然而它不给人吃、看见刀就跑得老远,也不能怪领导恨它入骨了。
历史上真有这位猪兄存在吗?不知道。但可以确定的是,王小波希望它存在,而且王小波自己也身体力行地向我们示范了如何“跳出”栅栏。
王小波年生,莫言出生于年,到二十世纪70年代,两人都正处于血气方刚的年纪,却生活在牛鬼蛇神当道、人不说人话、人不做人事的时空里。生活空间、思想空间、表达空间被压缩到格子间大小,也难怪会不约而同地生出“猪圈”与“猪”的想象了。
今时不同往日,国家发展了,城市里不太看得见猪了。只是干净有序的城市里,偶尔有“羊”,因此也多了许多力大无穷、敬职敬业的捉羊人。猪猪羊羊人人,恍惚间真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物种了。不知是否有人像莫言一样会幻想自己变成羊,又或者像王小波一样期待一只特立独行的羊?
说了这么多猪啊羊的,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和我一样饿了。午饭时间快到了,居家的该做饭了,没居家的记得点个外卖。
ZoeWan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