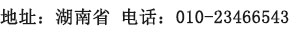李文亮医生走了。
书单君一夜难眠。我相信很多“书米”和我一样,悲伤,哀恸,辗转反侧,深夜痛哭,只能在网上以各种方式寄托哀思。
但还有一群人,他们连可以悲伤的时间都很短,然后必须擦干泪水,再上前线。
这些人,就是李文亮的同行——中国医生。
他们最能体会到李文亮的痛苦与坚守,也最能理解他的坚强与脆弱。
因为职业的特殊性,医生经常被称为“白衣天使”,但脱下白大褂,他们不过是跟我们一样,会哭、会累、会被传染的普通人。
我们给了这个群体太多的期待,和太少的了解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,书单君想跟大家分享一部关于医生的纪录片,看完这部片子,书单君只有一个想法——中国的医生,太难了。我们在反抗,医生却一直是“如果我死了,就是浪费国家资源。”——脑血管医院时,经常听到医生说“一定要按时吃饭,早点休息,这样身体才好得快。”这句话医生嘱咐的最多,可是他们自己却做不到。排着长队的病人,动辄七八个小时的手术,还有各种突发的急诊,让“规律的三餐和作息”成为了很多医生遥不可及的梦想。对他们来说确实是福报,因为他们的日常就是。在众多突发疾病中,心脑血管疾病是死亡人数最多的,短时间内得不到救治,就容易致残甚至致死,医院都为此设置了24小时绿色通道。朱良付医生(医院脑血管的主任)就是这个通道的组长。每次绿色通道有急诊,不管是深夜还是凌晨,医院来。有一次,朱医生的手术做到晚上12点,还有16台造影,全部完成后已经是凌晨5点。朱医生自己都说,“天天就这样作息不规律,工作量大,我就担心自己会突然死掉。”但他不能死,因为无论是家庭责任,还是医疗责任,他都还没有尽到。像朱医生这样的主任医师,差不多要用25年的时间才有可能培养出一位。44岁的朱医生说:“如果我死了,就是浪费国家资源。”看到这句话,书单君不禁想到了前段时间,被患者砍断手臂神经的陶勇医生。医院的眼科主任,本来是全国顶尖的眼科医生。年仅39岁就已经是硕士生导师,获得3项国家专利、发表了48篇SCI论文。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眼病患者,在陶勇医生的帮助下重获光明。在病人拿不起手术费的时候,他甚至还会给患者贴钱。就是这样一位心地善良、医术精湛的医生,却因为一次医闹,毁了。同事和学生去探望时,陶医生还安慰他们,让他们好好学习和工作。但没人探视的时候,ICU的保洁医生说,他在默默流眼泪。陶医生清醒后,口述过一首诗,他说即使以后不能再重返手术台了,也想组织一群盲童进行巡演,让他们赚钱养家。诗的最后一句是:“我把光明捧在手中,照亮每一个人的脸庞。”看病不是买卖“我们共同的敌人,是疾病本身。”——胃肠胰外科主任牟一平“我想要把你撕成碎片!”这句话是一个老太太对朱良付医生说的,她觉得“是朱医生把老爷子(患者)害死的”。她一边骂人,一边还说“我最近血压高了,你给我看看”。这个老太太也知道朱良付是好医生,但是这不耽误她投诉和告状。就像她知道,老伴是因为脑高灌注综合征(一种罕见但病死率极高的并发症)去世的,但是这不耽误她把责任推到朱医生身上。在医患关系中,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作为患者或家属出现的,所以我们对患者一方更容易感同身受:要早起排队,等很久才能见到医生。如果病情严重,每一天都在等待结果的煎熬中度过,结果出来之后又有新的问题要担心。手术时,家属唯一能做的就是盯着通知的屏幕,如果手术超时,心都要提到嗓子眼了。除了病情,医药费对很多普通家庭来说,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这些担心和焦虑,我们很多人都体验过。这种情感上的焦躁都可以理解,但我们同时也要明白:这些负面情绪,是疾病带来的,而不是医生,医生是百分之两百希望手术成功的。医院来说,医药费贵主要是因为仪器和用药贵,医生的工资并不高。但在那些“医闹”的人眼里,“我给了钱,你就要给我把病治好”。这句话放在商业逻辑里是没有问题的,但看病不是买卖。人体和医学都是非常复杂的,无论你给多少钱,很多疾病都会存在或大或小的治疗风险,再厉害的医生也只能降低风险,不能杜绝风险。哪怕几率再小,只要是发生了,对于病人来说就是%。关于医患关系,我很喜欢纪录片中,血液科学术主任孙自敏给出的比喻。在给一位十岁的血液病患者进行治疗前,孙医生是这样跟他们沟通的:“我们医护人员和家属、病人三方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,目的是一样的,只是分工不同。就像我们打突围战,能不能冲出去,你(患者)是战士,我们是制定方案的人,你爸爸妈妈是准备粮草弹药的人,最后成功肯定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,但关键的人是你。”医生是提供帮助的伙伴,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疾病。在这场针对疾病的战役中,有任何一方撤退,战役都无法取得胜利。有些痛苦,是注定要承受的“往往是医术的瓶颈还没遇到,人心的瓶颈就遇到了。”
——烧伤科医生徐晔
《中国医生》的第二集,医院一位烧伤病人的故事。
60岁的老刘因为煤气爆燃,全身烧伤面积高达95%,一同被烧伤的老伴,因为病情稍轻,医院。每天,老刘都要经受一次长达2小时的“酷刑”——换药,陪床医生徐晔要把他的伤口打开,上药,再包合。整个过程无比痛苦,接近“不可忍受”。有句话叫“往伤口上撒盐”,老刘的情况就是往全身撒盐。他受伤最严重的地方是双手,所以四天后的植皮手术至关重要。但每天的换药就要大几千块钱,手部植皮手术要两三万,因为烧伤面积过大,植皮手术要重复多次。整个治疗过程算下来,大概要花费多万。在整个治疗过程中,徐医生和家属做了三次比较正式的交流,每次交流的难点都是一个字——钱。徐医生希望至少能让病人做完手部的植皮手术,这对病人之后的生活,有非常大的帮助。而且创面如果不关闭,后期也非常容易感染。医院的基金会申请了2万的救助金。儿子考虑的则是,做完手术不可能马上走,后期还是一个经费问题。现在已经花了20万,手术后还要20万,而且老人还没有医保。本来之前他刚买了房子,还办了个小厂,投了点钱进去,但现在卖就亏太多了。“现在能借的都借了,还在网络上筹集了几万资金”。几十万的医药费对这个普通家庭来说,确实是很大的负担。最后,儿子刘某还是决定不做手术,直接出院。这个决定对于三方来说都是痛苦的,但这种痛苦,在当下是注定要承受的。得知病人强行出院的消息后,徐医生说:“我肯定希望他活下来,但是什么叫好,你把他治愈、出院,但他浑身是瘢痕,他的生命质量下降,他的家庭也会因此受到拖累,这是不是真的好,很难说。”一个月前,就在同一个病房里,徐医生的另一位重度烧伤患者,也因为同样的原因,家属放弃了治疗,最终病人去世。老刘走后,徐医生拍着病房里那张烧伤病人专用的翻身床,感慨良多。人生本来就是一场修行,对任何人来说都是。???写这篇文章之前,我跟一位做过肿瘤医生的“书米”聊过,他开玩笑说,“命短的不适合学医”,最普通的医生,也要本科5年+毕业1年后考执医证书,才能上岗。主治医师就更长了,至少要经过“5年本科+3年并轨+2年考试”,最快10年。这位“书米”最后选择了转行,因为“社会认可度不高,工作强度大,工资比高中同学还低。”前几天,他写了一篇关于医生的文章,里面说道:“医生是培养周期最为漫长的一个行业,当你拿起屠刀时,伤害的其实是千千万万的患者。当你拿起键盘时,请考虑一下,为了成为一名医生,他们已经失去了太多太多。”每一个医者都是普通人,但不是每一个普通人都会成为医者。
李文亮医生的去世警示我们,一个健康的社会,不能只有一种声音。一个健康的社会,不能没有医生。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之后,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理解医护人员的苦衷和价值,我们不能让医生既穿防护服,又穿防弹衣。
如果医生真的成为“高危行业”,以后还有多少人愿意学医?
我们都可以选择不做医生,但是,谁能选择不生病呢?主笔
燕妮编辑
黑羊
图源
《中国医生》
向医者致敬??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